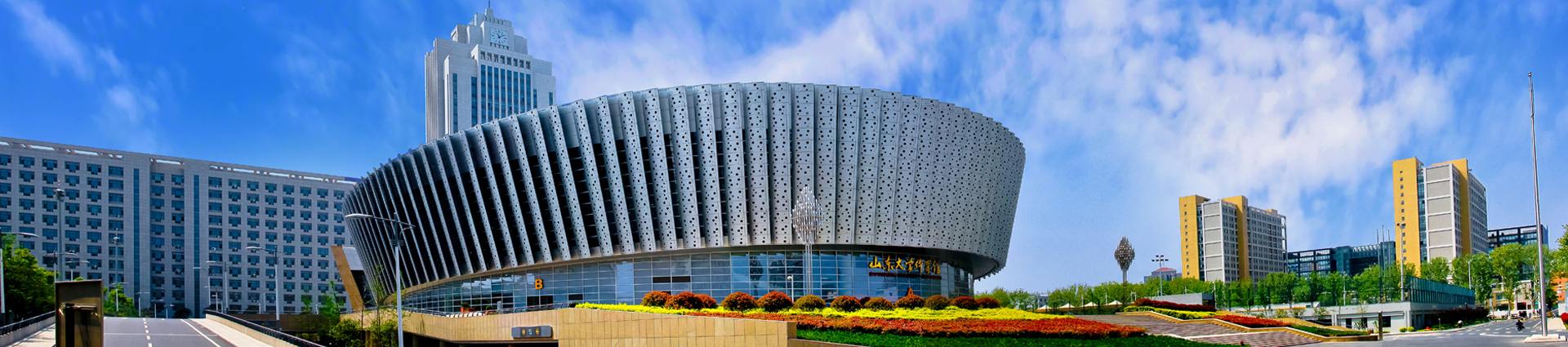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总体规划,仅提出6亿元资金,而现在实际开销已超过120亿。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而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又再次面临着远走他乡的困境。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总体规划,仅提出6亿元资金,而现在实际开销已超过120亿。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而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又再次面临着远走他乡的困境。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