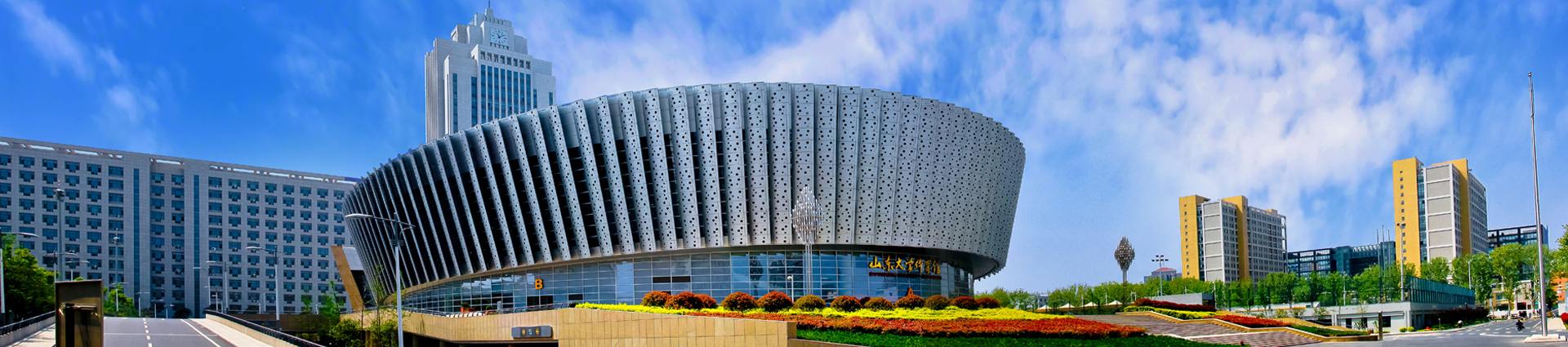核心提示: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核心提示: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很多亲历者后来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莱茵大营”中人员的死亡。
战俘施畔纳在1995年出版《眼泪、死亡和无尽痛苦》一书中回忆道,瘦成骷髅般的他有时在夜晚看着天空想象着自己何时也在一天的早上和其他死去的战友一起被人抬走,然后被放进营地外路边的尸坑。
来自布德利希战俘营的老兵耶格说,每天晚上死在地洞里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些地洞后来都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推平了。
战俘格利斯海默在个人回忆录《美国战俘营的地狱》中写道:死人被铲车推进战俘营外面的尸坑里,分5层摞成一长排,盖上了土之后就完事了。
战俘韦尔纳在1998年出版的《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中说,住在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附近的居民证实,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120-180具的尸体被运走。韦尔纳据此估算,在他呆过的这座容纳了13万战俘的大营里约有1.5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1.5%。如果加上在阴雨天气被坍塌地洞活埋的死者,死亡率应在15%。鉴于其它“莱茵大营”的状况也不可能比布瑞曾海姆战俘营的待遇更好,韦尔纳给出了一个恐怖的算式:500万人乘以15%,等于75万战俘在“莱茵大营”里死亡。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了一本叫作《有计划的死亡》的书,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巴切克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以及后来移交给法国后死去的德国战俘的总数为80万到100万人。其中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这个数字和原战俘韦尔纳的结论不谋而合。巴克切认为,掌握真实数据的是美国,但记录此类信息的文件或者已被毁掉,或者已被修改,或者至今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战俘营里简易帐篷,和难民营完全一样(来源:资料图)
“莱茵大营”之谜
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带有明显的“西贵东贱”的特征,这就导致了纳粹德国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对战俘的不同待遇。对于在东线俘虏的敌人,纳粹几乎是为所欲为,而对在西线俘虏的敌人则基本上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行事。
在“二战”时的欧洲西线战场上虽然也发生过敌对双方互杀俘虏的个别事件,但总体上说双方在对待战俘的做法上都还算守规,因此,德国兵在必须缴枪投降的时侯,无不希望成为西线对手的战俘,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权利要求西方的对手给予他们“日内瓦待遇”。
所谓“日内瓦待遇”,是在一些军事大国的主持下,由世界众多国家共同约定的一些战争时的游戏规则。在“二战”期间适用的“日内瓦待遇”是从1929年7月27日开始生效的两个国际公约规定的,其中的第一公约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是《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的实质在于要求签约国以本国军人的相关标准善待被本国关押的敌国战俘,对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公约中的以下规定中明确感知:
第10条……至于宿舍的总面积、最小限度的空间、起居设备和材料,其条件应与收押国安置自己部队的条件相同。
第11条……战俘的口粮在数量和质量上应与收押国自己的部队相同。……
第12条服装、内衣和鞋袜应由收押国供给战俘。上述衣物的经常更换应获得保证……
第13条各交战国应负责采取一切卫生措施以保证战俘营的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
在对公约的遵守上,德国兵有理由相信美国人做得最好,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美国是时尚文明的代表者,是国际间缔结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的主要推动方,又是最具有善待战俘的物质实力,更况且美国人对德国并无深厚的历史积怨,不象英国和法国那样上百年来恨德国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也就难怪“降美不降苏”成了面临失败时的德国兵的普遍心态。
我在柏林工大的博士导师克拉茨教授就曾是被美军收押的战俘。但是,他为我展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教授说,美军从阿登战役后开始大举深入德国本土,从那时起,他们对德军俘虏的管理就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很多德军的战俘被送到美国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洗脑”。但是后来德国的大势已去,美国人不再需要借“优待俘虏”的做法来瓦解德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德国投降前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面对人海一般的德军俘虏,国际公约象用过的抹布一样地被抛在了一旁。如果说美国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逾越日内瓦第二公约,那就是他们好歹还没有对这群战俘大开杀戒。
1945年4月,德国空军第8信息学校的学生连奉命阻击逼进哈勒的美军装甲部队。小兵克拉茨参加了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结果他“幸运”地成为了美军的俘虏。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没有在德国即将投降之时倒在战场上,而且他缴枪的对象是美国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素来以讲究人道主义著称的美国人会为德国俘虏准备了一所在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莱茵大营”。
他说:“4月到6月,是我战俘生活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美军在向德国本土纵深推进过程中不断看到纳粹集中营里的罪行,他们为之震撼,也更加憎恨他们的敌手。这种憎恶在战争结束后就很自然地延伸到德国战俘身上。我们的战俘营(就是所谓的‘莱茵大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万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离。因为战争后期德国的老兵已经所剩不多,我们这个方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的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因为食品紧缺,美国人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给战俘开饭的形式。他们派出一批士兵面对面地站成两排,中间留一个通道。每个士兵面前摆放着一张堆放着某一种食品的桌子。食品有奶酪、巧克力、肉干和面包,但没有任何水果和蔬菜。开饭时他们命令战俘们以方阵为单位一批批轮流跑步过来取食品。速度要求很快,两旁的美国兵还不停地大吼‘quickly,quickly!(快,快!)’我们不许带容器,又没有时间挑选,只能一边奔跑一边迅速用双手去抓能够得着的一切东西,能抓多少算多少,反正最多也就是把双手占满。这种开饭的方法一是让人吃不饱,再有就是吃不好,有时赶巧连续几次抓回的都是巧克力或奶酪。因为长期没有蔬菜和水果吃,战俘们普遍大便干燥,经常互相帮着往外抠大便。我受不了这份罪,就尽量少吃或干脆不吃东西,所以身体变得特别虚弱。
“饮用水受到严格限制,大小便和垃圾也没有专门的地方和处理措施,环境一天天变得恶劣和肮脏起来,为此美国兵必须采取大面积消毒措施来防止瘟疫的发生。美国人还禁止我们对外通信,我的父母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一直不知道我的死活。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人今天会怎样对待那些塔利班战俘和伊拉克战俘的。直到1945年末的圣诞节,我们第一次被允许往外寄明信片。”
“德国军人在战争结束时的去处基本上都是战俘营。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1945年7月,我们被转移到法国,仍由美国人看押。进法国后常有老百姓向我们的队伍吐唾沫扔石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至今还很深刻的印象:在行进中,路边有个在母亲怀中的法国孩子向我招手,我刚刚要抬手和他打招呼,就见那个母亲一把按下了孩子高举的小手,接着就把一个耳光打在孩子的脸上。法国人对德国的仇结已拉得太紧了。我入伍前曾见过大批被俘苏军。德国老百姓见到他们的惨状很不忍心,很多人把脸转过去。没有一个人向这些人扔石头或做出其他举动。这是民族性格的差别。‘二战’时,德国人会在军队的整合下充满攻击性,却不会以平民身份去攻击和羞辱失去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
“我们被转移到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正规战俘营,终于有了帐篷住,但还是没有被褥,只能拿废纸壳箱铺地当褥子用,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得到了被子。在那里我们开始接受民主教育。老师是那些到美国接受过洗脑的德国老战俘,每天喋喋不休地讲美国的生活和民主。我们听讲只能集中精力于前一半时间,后一半时间就在盼吃饭,因为肚子太饿了。我们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中午的到来,因为午餐有一顿热汤喝,而晚饭我们只能得到一片面包。夜里饿得睡不着时,我们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凑到一起精神会餐,谈怎么做糕点,放多少油、多少蛋、多少奶,很多人还用笔把别人的绝活记录下来。聊着聊着,口水就淌出来了。有的人饿急了,就去垃圾桶里翻美国兵吃剩的香肠和奶酪。
“看守我们的美国兵很不相同。犹太人士兵态度最凶,而黑人士兵对我们学生兵通常都不错。他们是我最早接触的黑人。
“我们的帐篷出口处有一个新闻布告板,每天在上面写些世界上新发生的事。这块小黑板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里我知道了纳粹杀害了很多犹太人,知道了以色列国的成立,知道了柏林正由美、苏、英、法4国军队共管。来自柏林的战俘就到处询问这4大管理区是如何划分的,以便知道自己家被分在哪个国家的管区。战俘营的广播喇叭每天都一成不变地播放着同样的几首美国歌曲,我觉得自己听得都快疯了。
“在战争中,德国实行政治封锁和新闻管制,人们不了解政治,也不敢谈政治。在战俘营中我终于知道了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罪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屠杀平民的行动和战争毫无关系,那么犹太人到底怎么得罪我们了?
“开始遣返战俘了。先释放的是有职业履历和特长的人,因为战后德国恢复生活和建设需要这些人。战前的面包师、工匠、渔夫、裁缝、司机、会英语的,一个个都回家了。我们学生最倒霉,什么也不会,只能看着别人回家。12月我被转移到法国凡尔登,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开始能吃饱肚子了。5月28日,我获得了全部释放返乡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释放证及体检证、身份卡、职业推荐信和原士兵证。只有这些材料齐全,被释放者才能在回乡后重新注册户口,领取生活品供应卡并寻找职业出路。”
说到这里,教授展示出一张纸,那是美军的警务监禁局的推荐信,是用打字机以英、德两种语言写成的,内容是:
被俘士兵海尔穆特·克拉茨,战俘号:31G3131232,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属我局管辖。在此期间,他作为厨师的工作表现使我们极为满意。他一贯令人信任,诚实可靠并且能干。在此我们特向有关部门推荐克拉茨,并请求对他重返平民职业领域的活动给予所有可能的支持。
带着这张推荐信,教授在1946年6月终于返回到柏林的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教授的这段回忆,使我对“二战”时的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给予德军战俘的待遇状况产生了兴趣。经过大量查询和后续的访谈,我发现教授所排列出来的待遇水平顺序(即英国较好,美国较差,法国差,苏联极差)并不十分准确。在战俘待遇的优劣比较上,英国最好,苏联最差确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就在于美国和法国这两家谁应该排在老三。教授没有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呆过,很容易根据德、法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来判定法国人对德军战俘的态度,认为一定会比美国人更狠。但根据史料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法国军方虽然做过一些报复式的,情节严重的虐俘行为,但其规模和程度上都难以和美军的“莱茵大营”(即教授住过的美军露天战俘营)相提并论。
在1945年2月上旬,落在美军手中的德军战俘的总数大约为30万人。对于德军当时的剩余兵力,美国人心里是有数的。此刻德军的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大约还有700万之众,尽管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但只要希特勒拒绝投降,盟军方面要想吃光这支顽强的军队无疑是需要时日和付出的。为此,美、英两国共同拟定了一套对德军俘虏的处理方案,准备把俘获的德军士兵逐批运送到已被解放的法国北部地区拘押。但是,接下来的战争进程发展之快大大超过了盟军的计划。在3月份的莱茵河西岸战役中,大批东撤的德军因无法跨越莱茵河(河上的桥梁大多被毁)而被美军俘获,加上在鲁尔包围圈里被俘的德军B集团军的32万人,总计57.5万的德军士兵成了美军的战俘。面对如此多的战俘,原定的安置计划在组织工作上遇到了瓶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建立露天大营,就地安置战俘,于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莱茵大营”诞生了。
1945年4月,原本要把盟军赶出德国本土的德军B集团军的21个师约43万人在鲁尔地区陷入盟军的大包围圈。4月21日,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签署了B集团军就地解散的命令后自杀,32万德军士兵就此成为了盟军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安置在莱茵河畔的临时露天战俘营,“莱茵大营”由此诞生。4月25日,在雷马根的“莱茵大营”的岗哨位置上一眼望去,密集的战俘人群浩如烟海。
“莱茵大营”的英文名称为“RhineMeadowCamps”,德文为“Rheinwiesenlager”。直译为中文就是“莱茵草地营”。这个名字听上去颇为优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的广阔草滩上的野营渡假。但实际上“莱茵大营”是在莱茵河西岸地区的平坦空地上,用铁丝网分隔开来的一系列巨大的露天战俘营。设置这样的战俘营的第一考虑是用莱茵河阻断战俘向东逃往德国腹地的去路。其次是充分利用莱茵河流域的宽阔平原,用最省力的方式容纳最多的战俘。后来的战争局势证明,就地安置战俘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随后的德军被俘人员的数字呈爆炸式增长,把这些战俘及时疏散到法国去已变得很不现实。(待续)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军老兵寻访录》,作者:朱维毅,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