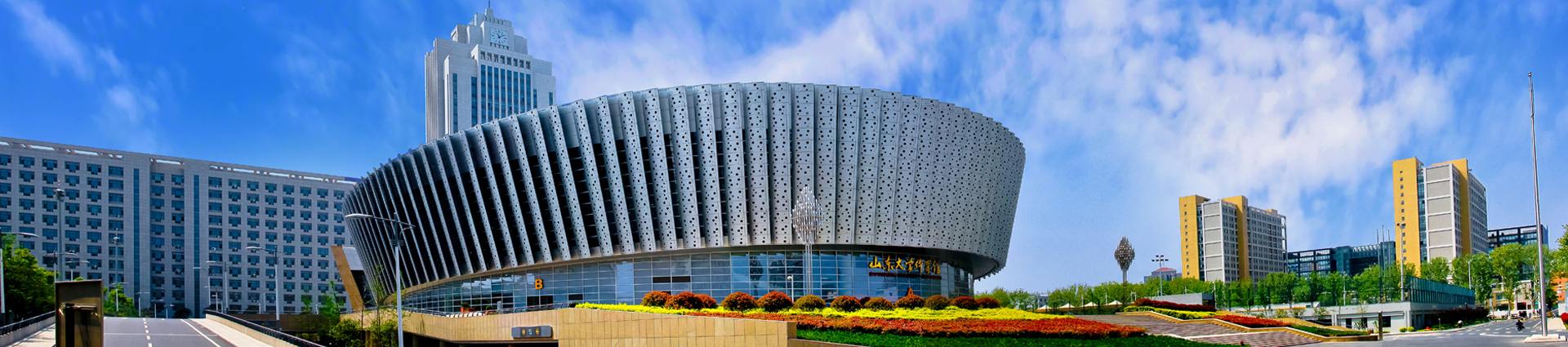作为一个移民种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一般都属赌博、斗殴之类,而非盗窃、诈骗或武装抢劫一类的职业犯罪活动。19世纪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绘为“诚实不亚于鲁莽”的人,就是说,别人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别人来,他们不太会“捅娄子”。他们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动不动就吵得不亦乐乎,打架对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带一把刀或一杆枪,谁敢攻击他们,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人认为,他们在19世纪大批迁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后,那里的打斗事件就减少了。在爱尔兰人称霸于移民“集居”的贫民窟时,无端殴打陌生人或向过路人行窃,乃属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个不肯让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时,搞这类欺侮行人的小动作就十分危险了。
职业性的犯罪活动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特别是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并不参与这类活动,虽然他们也遭到连累,被无辜地打上黑手党的印记,岂不知他们自身就是黑手党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此时尚未发展到后来在禁酒运动时那样的猖獗程度。更何况,在意大利移民来美的那段时期,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头子大多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各移民种族按照美的时序而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带有继承关系,这后来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种族一样,较高的犯罪率都发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间。在纽约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率在两代人之间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当中,有一项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意大利移民的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不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学校里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孩子们由于在两个世界里长大,也就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这固然有利于他们向上流动,却也在家庭里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时常造成个人内心的矛盾。
家庭依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仍是忠诚的归宿。离婚、分居或抛弃妻室,在意大利人当中仍属罕见,这与早先的爱尔兰人或20世纪的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家朴实无华也仍旧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风尚。此外,意大利人的家庭大体上也还是父亲说了算,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多由母亲做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挣得的大部分收入。
在叙述美籍意大利人的发展史时,人们容易忘记这段历史的代价。约瑟夫?罗普里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过意大利人的苦楚:“愤怒的爱尔兰人;傲慢而又惊慌的‘美国人’;贪得无厌而又诡计多端的包工头;不可靠的职业;逃不脱的工伤事故;在老板的大声呵斥之下,从早到晚弯腰低头,抡动铁锹干个没完;带有侮辱种族色彩的玩笑和脏话;贫民窟斗室之内的恶心气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学回家后希望知道为什么做个‘热那亚人’是不好的……”等等,意大利人什么痛心的事都碰到过。
教育
美籍意大利人对接受正规教育是很迟疑的,认为它会威胁到家庭的价值观念,并使孩子失去就业的机会,无法找工作赚点钱来贴补家用,在经济上划不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意大利人都高度重视实用知识,但正规教育却被认为是不实用的。在意大利南部,对于迁居美国的那些阶层的人们来说,正规教育确实是不实用的,从来美的第一代移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来看,正规教育的实用性也不怎么明显。在那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工作机会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或领会的范围。《教父》一书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本人就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说过:
母亲希望我能在铁路上找个书记员的差使。这是她的最高理想,达不到这一点她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一字不识,在意大利时是个农民,相信只有贵族子弟才可能当上作家。
家庭对正规学校教育的支持不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逃学率高,放学后要干活,一到法定年龄(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立即退学,等等。此种风气不仅反映出父母的想法,孩子在学校里也有其难处。意大利移民的孩子在美国的学校里,从言语、衣着到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一切都使得他们成为别人嘲讽的对象,诚如当时一位人士所言,学校的教员也对招收这些孩子入学感到“遗憾和不安”。挣钱的诱惑力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芝加哥,出生于美国的意大利人子女,其辍学率甚至比在外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子女还要高,而后者在就业方面是不如前者的。
按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狭隘观念,“要上学而不愿工作的儿子是个‘坏儿子’,要读书而不愿帮助母亲做事的女儿是个‘坏女儿’”。受教育意味着和家庭离异。坚持深造的个别学生,内心感到矛盾和自责,妨碍他们和那些升学受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及鼓励的人进行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大利儿童时常在班上年龄偏大,而且这种偏大的程度超过其他多数主要移民种族的孩子。19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南部意大利移民的子女有63%的人,比所在年级的“正常”年龄大。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是7岁或7岁以后才入学的,但即便是在6岁入学的儿童当中,也几乎有半数人在被调查时落在正常班级的后面。
一般来说,移民子女离校辍学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意大利人的子女当中显得特别突出。1908年,纽约八年级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三年级学生人数的1/3。而对意大利子女来说,部分地反映出教育设备之不足。学生只有在达到给定年级的标准时才能获准升级,“超龄生”和“留级生”比比皆是。当然,和各移民种族的子女相比较,意大利儿童的“超龄生”和“留级生”的比例又是偏高的。在那一时期,读完中学的俄国犹太人子女占16%,德裔子女占15%,爱尔兰裔子女不足1%,而全纽约市的意大利裔子女读完中学的却连一个也找不到。到1931年,纽约全体中学生读到毕业的占42%左右,而美籍意大利人的子女读到中学毕业的却只占11%。
意大利人子弟在公立学校的成绩是如此之差,致使当时许多“专家”们断言他们在遗传上和智力上是属于“劣等”的。在那一时期,意大利裔的成年人和少年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都很低(不比今天的黑人高),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在近几十年来就有所提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籍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一直在全国平均数的上下浮动。
随着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内部也产生了差别。在起色不大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求学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被视为可疑之举,学生没兴趣和家长认可的逃学是两个主要问题。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上大学的不如在一般美国人当中那样普遍,尽管差距已不如过去那么大。即便是在那些到高等学府去深造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老的传统习惯仍在各方面留下它的痕迹—例如,阅读习惯差,或情绪上有矛盾,觉得脱离了家庭的轨道似乎就“背叛”了家庭等。传统上对教育所持的功利主义观点,可以从美籍意大利学生所选择的专业上看得出来,他们一般都报考“实用的”或应用的学科,比如男的读工程,女的选师范。
工作
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都是非熟练劳工,而第二代人就在职业的阶梯上爬高了一步,就业的范围和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第一代移民在世时也有向上流动的。
1905年在纽约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当中,从事白领工作人士的比例依其居美时间的长短而异。但不管在美时间的长短,有40%的人属非熟练工人。居美时间不足25年或达25年的人,从事高级白领工的实属微乎其微(即不到2%)。居美达25年以上的人,有14%从事着高级的白领工作,但这个比例不但反映了时间因素,也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1880年之前迁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就那些居美不足25年或长达25年的人而言,从事一般白领工作的比例有一个幅度,具体说来,居美在7年以下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占9%,居美在15~25年之间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则高达24%。在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几乎有2/3的人在1910年是低层次的体力工人,但这批低层次的体力工人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其比例就下降到了38%。该市1910年意大利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只占12%,但在这些人退休之前,这个比例就升高到37%。
代与代之间的职业变化也反映出美籍意大利人地位的上升。在纽约,1916年意大利裔工人约有一半是干体力活的,但到1931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了31%。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人当上了电工、油漆工、承包商和工头等。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人开始在服装行业取代了犹太人,后者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意大利人也进入了市政管理人员的行列,起步时是小股的,并从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19世纪90年代在芝加哥,意大利人当清道夫的有100多人,其他还有人当上了下水道挖掘工、垃圾搬运工,也有人在各种建筑工程或维修部门找到了差使。19世纪末,有3个意大利人在芝加哥当上了警察,其后不久又有几个人当上了消防队员,这些数字虽然不多,但一直在增加,20多年之后,就上升到好几十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做小学教员的仅10人左右,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数字就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到42人。在意大利裔人口显得多得多的纽约,意大利人充当教员的在1905年也只有200人出头,1915年增加到400人出头。相比之下,早在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工的意大利人就有8000人之多。同样在旧金山,意大利裔的市政职工多是清道夫(有人说他们在这里“享有垄断权”),下水道、自来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挖掘工,也在桥梁、运河及港口等建筑工地上和维修场所干活。在全美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一如栖身于贫民窟的其他种族一样,美籍意大利人也不断地受到改革派人士的怂恿,让他们到农村去扎根。也正如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一样,意大利人基本上对此不感兴趣。多数人没钱购置农场,不少人打算返回意大利,很少有人愿意到那些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农场上去了此一生,尤其担心在那里甚至连“遥远”的邻里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当然,也确有某些意大利人下乡了,那是集体去的,大多是在农忙季节跑到乡下打零工,有的则办起了乡村企业。
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北部意大利人变成了种植水果、蔬菜和酿制葡萄酒的企业家。在世纪之交,加州的意大利人有半数在从事农业,这与全美各地的意大利人普遍都在都市就业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为加州的农业投资提供财政服务,A?P?贾尼尼建立起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银行—美国银行。另一个由北部意大利人早在1860年就开发出来的农业区是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也搞得十分成功,并与当地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其他州也有意大利人办起来的小型农业社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州西北部。定居在这些地方的多属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发家的速度慢,遇到当地民众的抵制也多。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擅长于耕作贫瘠土壤的经验,使他们敢于购买被当地美国人视为“无用的”贫瘠土地,并将之变为良田。这样,许多开始时十分贫穷的南部意大利人后来就成了地主,为国家增加产出,也使他们本身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最终也被接纳为这些地区企业社会的一部分。
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意大利人在农业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愿意比别人更加卖力的苦干精神。许多意大利裔农场主都是从农场劳工和交谷租农干起的。由于缺钱,甚至购进低价的荒地和肥料,垦伐点林地等等,都时常需要他们不分昼夜地苦干,打零工,全家操劳,长年的积攒和借债,才能最终把借贷偿还清楚。在某些地区,比如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意大利人后来终于在当地的水果和蔬菜种植及经销方面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职业上,意大利人赶上了爱尔兰人,而在业主人数所占的比例上,则超过了他们。在1909年,波士顿的意大利人有22%是经商的,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经商的只占5%。到1950年,这两个种族的职业分布几乎毫无二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籍意大利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来美的时间却比意大利人早30多年。
意大利人多年来借以发家的那些渠道,一般都不要求受过正规的教育。美籍意大利裔工人逐渐掌握了技术,其工资所得也超出了单凭他们的正规教育所达不到的水平。极端的肯干一直是他们发家的强大力量,普遍很低的酗酒率也使老板觉得他们是可靠而又可取的雇员。有趣的是,意大利人滴酒不沾的在当时(乃至现在)极少,吃饭时都会把盏小饮一番(有时连小孩也喝上一点),但喝醉却是禁忌。
按美国的普通标准来衡量,苦干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不能混为一谈。所谓事业心,它牵涉到一系列具有既定目标的前进步骤,通常从大学就开始,其感情投入的程度也时常会和对家庭的承诺相冲突。此种职业进取精神在美籍意大利人当中形成风气,但进程是缓慢的。为家庭多干、苦干,向来是意大利人的一种气质,为工作而牺牲家庭,则为意大利人所不取。美籍意大利人世世代代都乐于在文官体系中供职,上班时间固定,恪尽职守自会得到报偿。而耗尽精力和时间的职业,比如当经理或做学问,意大利人向来不敢问津。
社会组织
与意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化,还有他们在社会上的差别。甚至在各阶层中,家庭一词的意义也变得不完全相同了。在意大利裔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亲戚之间的拜访频率仅略高于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走访亲戚的频率,仍是其他美国工人阶级的两倍。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开始重视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子女送到教区学校就读。由于意大利裔充当了教士和修女,学生家长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样,害怕其子女会在教区学校里“变成爱尔兰人”。
多年来,家庭的人口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在1910年,美籍意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国家庭人口的平均线之上,但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夫妻的子女数量已经比其他美国人要少,且只相当于早期意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岁左右的美国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而同一年龄段的意大利裔妇女则平均有5。5个孩子。到1960年,此项全美平均数是3,而对美籍意大利妇女来说,则只有2。4。曾是美国各种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意大利人,现在则和犹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变得最少。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在意大利人参与其中之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美国早就存在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犯罪团伙的头目多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付诸实施之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此时又适值意大利后裔大批加入了犯罪团伙的行列。偷运私酒及违禁开设秘密的酒馆(通常又和赌博或卖淫相勾结)成了赚大钱的生意,而且也是竞争性极强的生意。意大利裔的犯罪头目在这种暴虐而殊死的竞争中,具备两条足以决定胜负的长处:第一,他们在贩运私酒时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第二,正如家庭忠诚对一般意大利社会生活是关键因素一样,他们在营运私酒时,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风声。从事一种生死存亡的买卖,头脑清醒和家庭忠诚是两大格外重要的条件。
和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人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与籍贯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从事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家庭,都来自西西里(现在仍然如此)。西西里的黑手党传统给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辛迪加提供了结构框架,然而美国的黑手党却既非西西里黑手党的分支,亦非其简单的移植。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的既存事实,自有其一套机构,美籍意大利人实际上不得不经过一番较量,才得以打入其中。美籍意大利裔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有共同的祖籍,此点可由这样一个事实加以证明: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时期,美籍意大利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上的犯罪率仍比其他美国人偏低。
对于美籍意大利人来说,正如对其他一些缺少发家资本或教育传统因而无从在商界或学术界平步青云的种族一样,体育、娱乐圈和政治,也像犯罪活动一样,都能给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美籍意大利人进入体坛的时间,要迟于爱尔兰人,而且从未在这方面像爱尔兰人那样取得过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像乔?迪马丘、洛基?格拉齐亚诺、文斯?伦巴第、约基?由拉和洛基?马齐亚诺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确实代表着意大利人对体育界的重大贡献。在音乐界—古典的和通俗的—意大利人在美国也和在欧洲一样,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在古典音乐方面出过像恩里科?卡鲁苏、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安娜?莫弗以及贾恩–卡罗?梅诺梯这样一些大家。流行歌曲明星有弗兰克?辛那特拉、佩里?科莫、迪安?马丁和托尼?本内特,这些人也只是著名美籍意大利人歌唱家的一长串名单上的几个罢了,其中许多人改用了英国式的名字,如康妮?弗兰西斯或勃比?达林等等。
美籍意大利人在政坛上发迹较慢,但最终也造就出市级、州级和全国性的政界名人。第一位意大利裔政界大员是费奥莱罗?H?拉瓜迪亚,此人是深知基层民众并有巨大号召力的极少数“改革派”人士之一。缺乏从政经验,缺乏种族内部凝聚力,是影响意大利人政治努力的两大障碍。直到本世纪初年,意大利选民区在政治上仍由爱尔兰人充当其代表。此种状况开始时并未遇到挑战,后来当意大利人崭露头角时,才巧妙地使选区分化,并逐渐控制了自己的选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意大利裔政客才掌握了与爱尔兰人或其他更富于政治经验的种族成功地进行较量的本领。卡尔明?德萨皮奥在1949年首次以意大利裔的身份当上了纽约坦慕尼协会的首领,尽管意大利人早就是该市人口最多的种族之一了。然而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总能赢得本族人的选票。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拉瓜迪亚市长在1941年与爱尔兰裔对手(威廉?奥杜瓦尔)竞选连任时,也未能赢得纽约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犹太裔的纽约市市长候选人(阿布?比姆)也曾比其意大利裔对手赢得过更多的意大利人选票。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
今天,美籍意大利人在收入、教育、智商得分和其他许多指标上面,都与其他美国人大体相仿。最近对人口统计的研究表明,意大利裔家庭的收入,稍微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些意大利裔家庭大多都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大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生活开销)是普遍偏高的。近年来,意大利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其他美国人平均水平的12%,这一事实可能只反映了地区性或城乡差别。但无论怎么说,对于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其收入仍只相当于全美平均数45%的意大利人而言,能赶上全美平均数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人的崛起基本上并未借助于通常认为是必经之路的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职业。时至1969年,35岁以上的美籍意大利人比起同年龄段的其他美国人平均受到的教育,几乎要少两年,上过大学的也不到其他美国人的2/3。他们在专业人员当中或在其他需要受过教育的高级职位上,人数很少。在纽约市,意大利裔的专业人员,在比例上还不如黑人高。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大学里,意大利裔的教授人数一直很少。到1972年,年青一代的意大利人(25~35岁)在受教育的年限上赶上全美平均水平,在大学毕业率方面才接近全美平均水平。这种教育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人经济腾飞的结果—父母有条件让子女去读大学—而显然不是腾飞的原因,因为经济腾飞早就实现了。意大利人的收入在1968年就超过了全美的平均线。
美籍意大利人不仅苦干,而且也能攒钱。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大部分都是打算把家眷接过来或攒钱回国成家立业的男子—省下所得的一半是普遍现象。避免挥霍一直是意大利裔人士后代的一个特征。强调自立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拒绝接受政府给予他们的法定救济,甚至在收入低微时也保持良好的银行信誉,不热衷于政治或投机事业。
放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就可能会理解意大利人和黑人之间的今昔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了。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对黑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较少(特别是在美国南方),然而在目前,意大利人对黑人的舆论与其他白人相比,是很不妙的。黑人领袖所强调的种族进步之路,恰是美籍意大利人所排斥的道路,认为靠政府救济和特殊照顾违背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两个种族的生活作风也相互冲突。双方都视对方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是故意的侮辱,而实际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里,这些都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下述事实又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其他白人的惯常做法不一样,意大利人在黑人迁入其地段时,恰恰不愿意搬走,坚持住在原地(哈莱姆至今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的社区),从而使他们比其他种族有更多的机会和黑人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与美籍华人却并非如此。华人虽然肤色不同,但其价值观念和生活作风却与意大利人并无相悖之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远胜过他们与爱尔兰人的关系,爱尔兰人的生活作风—特别是在19世纪—就是20世纪城市黑人生活作风的先兆。总而言之,笼统地用“种族主义”这个字眼来解释,无法找到族际间敌对关系的缘由。
意大利移民及其后代尽管如此强烈地抱着祖国的文化特征不放,他们却未能相应形成全美意大利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对意大利的民族感情就更弱了。在日益美国化的过程中,美籍意大利人也多少意识到他们在美国是个单一的种族群体,对祖国意大利也有某种关切感,但与美籍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操心程度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美籍意大利人曾一度对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感到一阵子欣喜若狂,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意大利裔之外的美国人也曾怀有同样的情绪,当时报界对墨索里尼的有利报道就可证明。从未有人当真要把墨索里尼的意识形态移植到美国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籍意大利人欣然地参加了美军进入意大利的战斗,并未产生爱国心方面的矛盾感。他们在美军中的存在很可能促进了意大利民众对美军的友好态度。
美籍意大利人新近的种族认同感,与某些其他种族那种抱成一团的态度或在政治上清一色地选举本族人的做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能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完全可以指靠本族选民的选票。1965年在争取提名为审计官候选人的预选运动中,马里奥?普罗卡西诺将本族的选票丢给了犹太裔竞选对手,其所以能获得提名,只因为他在犹太人选区反倒赢得了多数选票,岂不怪哉!在后来的一次选举中,普罗卡西诺获得了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但那显然不是因为他有个意大利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意大利裔选民的利益十分重要。在1962年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竞选活动中,意大利裔候选人约翰?伍尔普在与他的老对手、盎格鲁撒克逊裔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角逐中,只赢得了51%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
意大利人在政治上的成功相对来得较晚。第一位意大利人当选为参议员是在1950年,第一位意大利人被任命为内阁成员是在1962年。某些意大利裔候选人赢得过本族选民的多数选票,某些犹太裔候选人照样也能赢得多数意大利选民的选票,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竞选总统时曾在马萨诸塞州获得意大利人85%的选票。一般说来,在意大利选民当中,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得人心,但两党的极端自由派—如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在意大利选民中遭到惨败。
尽管纽瓦克和费城等地黑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对抗,曾被广为宣传,然而这些肤色及种族间的冲突,也是因对社会问题比如警察权力和控制犯罪等看法上的强烈分歧所致,当然与族际敌对情绪也难以截然分开。在1968年,对民权运动持反对观点的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仍在纽瓦克获得21%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克利夫兰获得29%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全美获得10%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相比之下,除去南部,他只获得全美8%选民的支持。但是也就在同一年,竞选马萨诸塞州美国参院议员的共和党黑人爱德华?布鲁克,获得该州意大利裔选民40%的选票,比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马萨诸塞州赢得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还要多。1970年在纽约,一位竞选州府公职的候选人,在纽约州西北部获得大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而在纽约市他就不行了,因为该市的黑人和意大利人在地方问题上时常是壁垒分明的。与1928年南部—这里的天主教徒极少—不投阿尔?史密斯的票因而也是反对天主教徒的情形相反,意大利人和黑人在政治上的对抗,看来主要发生在那些二者之间因利益或价值观念发生现场冲突而使他们各执一端的地区,而不主要是因为存在一般的种族主义,一般的种族主义应当适用于不管附近有无黑人的任何地方。
美籍意大利人长期以来对学校、民居计划和其他局外人硬性规定的“美国化”计划,尽管感到愤懑并进行抵制,但他们却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变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尤以其爱国主义著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士兵仍以种族划分编制时,美籍意大利人应征入伍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最终的牺牲人数在比例上也同样高于其他种族。尽管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4%,但在战时的伤亡人数却占到美军伤亡人数的10%。
从长远观点看,确实证明美国是从意大利来到这里的那些人的机会之邦。但是把机会变成现实,也的确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并具备持久的毅力。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用他们的双手获得了新生,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双手说“美国就在这儿,这就是美国”时,他们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