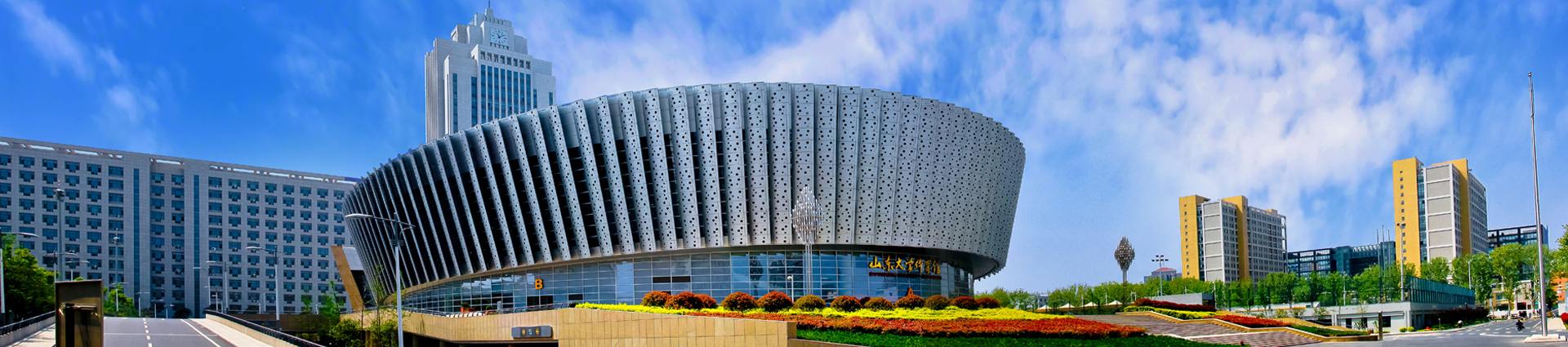宏疆村是中国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村里人大多靠耕地、打渔或养猪为生,2010年一个小伙子因勤劳致富当选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十佳青年”,被当地人视为值得敲锣打鼓庆贺的大事情。然而,在这个只有165户人家的小地方,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在内,大部分村民都有着深蓝色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和浓密的络腮胡,这和一河之隔的俄罗斯人非常相像。
他们的祖辈就是俄罗斯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一场难民潮,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更是令很多家庭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苏联人只有越过黑龙江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
一个叫葛金丽娜的贵族女人就把1岁多的孩子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冰封的江面,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山村。她嫁给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人,并为儿子改名徐维刚。“户籍证明”上,小男孩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
如今,88岁的徐维刚是宏疆村里所剩无几的拥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虽然母语对他而言已经成为远去的记忆。偶尔,他会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那啥,我叫安德烈。”
但大部分时候,很多人对自己的外貌异常敏感,他们憎恨被称作“二毛子”,这被视为比“骂爹娘还严重”的侮辱。关于“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这种问题也被视为禁忌,他们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国家叫做“他们”。不少村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中国人,尽快了断自己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总之,没有人会以血统为荣,正如同没有人愿意提及“特务村”这样的字眼。
“文革”期间,村里所有的混血儿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宏疆村也被称为“特务村”。一个叫张运山的村民,曾在抗战胜利后迎接入境苏联红军,因此被打为“苏修特务集团”的头头,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打到他跳井自杀。其余的成年混血村民因为长相被关在牛马棚里,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我跟我妈说,你上这边来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77岁的徐维义是葛金丽娜生下的7个混血儿之一。
建国初期的宏疆村最多时曾有21个苏联女人。她们不少人和葛金丽娜一样,都是贵族后裔。这些异国女子喜欢喝牛奶,烤列巴,会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每个周末,这些身材高挑的女人都会穿上蓬蓬裙,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口琴声悠扬。那时候,河对岸会邮过来瓜子和糖,她们的子女大多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影响着一江之隔的两个国家,边境一夜之间被封锁,在河对岸做生意、探亲的宏疆村人再也不能回到村里。
半个多世纪后,葛金丽娜和那些唱歌跳舞思念家乡的苏联老人都已经去世,并葬在了宏疆村。两岸的生活却早就热闹了起来,每月有大量的俄罗斯人要往返中国多次,带回廉价的牛仔裤、衬衫以及名为“阿迪多斯”的山寨运动鞋,他们甚至愿意坐上每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到中国理发,为孩子购买玩具。
曾经的“特务村”宏疆村也获得新生,并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虽然在这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了。有些村民会用《喀秋莎》的调唱民歌,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村民们叮嘱长着俄罗斯面孔的子女“一定要找个中国人”,在宏疆村的第四代混血儿里,最有出息的孩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并因为顺利入党而让父亲倍感荣耀。
“一次教训还不够?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 村民徐福胜经历过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那时候他只有13岁。
总之,他丝毫不喜欢自己的灰蓝色眼睛和大到或许能塞进一枚硬币的鼻孔,也不愿意再去寻找河对岸的亲戚,“以前跟人家一点联系都没有,还是给你安上罪名了。伤老心了,离他们远点吧。”
偶尔喝高了的时候,他才会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并想起自己的奶奶,一个叫葛金丽娜的俄国女人。
相关链接:
中俄边境上的“混血村”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在徐维刚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
“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的几个屯子里,87岁的徐维刚是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但在中国生活80多年后,俄语对他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大部分时间,他安静地叼着旱烟,偶尔开口,一口浓重东北的大茬子味。
“那啥,还认识我吗?我叫安德烈。”徐维刚咧嘴一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
“俄罗斯不承认他,中国也不承认他。”有村民咂嘴,“亏了是个傻人,啥都不在乎。”
“大清洗”和肃反运动
侄子们背后习惯管徐维刚叫“傻大爷”。
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有公开的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邻的中国。
彼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
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
“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边疆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
宏疆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老人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
边境的几个屯子里,苏联老太太们还在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列巴,喝苏波汤,小声唱几句俄罗斯民歌。但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
“特务村”
“倒也得能让人活啊!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是那啥来着?”稍显破败的土坯房里,徐福胜的大鼻子猛吸两下,“苏特!”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读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间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种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
边疆村的苗中林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个叫李荣贵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苏特”。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袁广荣的二哥由于在抗日战争后,迎接过入境苏联红军,因此更是成了“特务头子”。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后挖了个遍,连个轮子都没看见。“我哥进去的时候穿件白布衫,出来的时候,白布衫成红的了。整个人被打得实在受不了,跳井了。人死了,还不许家属哭。”
后来有村民觉得可惜,“其实他再坚持三天,就平反了。”平反后,村里的人给死去的村民开了追悼会,算是有了个交代。
有宏疆村村民透露,“文革”时,宏疆村和上道干村原本是一个大队,“文革”结束后,宏疆的混血人不愿意跟中国人住在一起,坚决要分家,“那些混血人可厉害呢,把牛马全抢了过来,公社的人气得够呛。”
“我是中国人”
那些血肉模糊的陈年旧事就像长在心里,随着时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疯狂地生长。
几十年后,当年13岁的徐福胜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小儿子还没找对象。“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重重地放下盛满酒的碗,再次瞪圆了灰蓝色的眼睛。
和宏疆村大多数混血人家一样,徐福胜兄弟几个一心想要断了自家俄罗斯民族的血统。他们的脑子里就一个信念:娶中国人,花多少钱也得娶。
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幸运地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罗斯。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过来。
村民徐月娥也叮嘱长着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徐福胜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指手画脚地管他们叫“二毛子”,“谁说这话给我听见了,我就冲上去问他,凭啥说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国人!”
就连平时的交谈中,徐福胜也习惯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俄罗斯叫做“他们”。“他们俄罗斯的事我也关注啊,日本外长今天到俄罗斯去了。”话题一转,徐福胜又说到中国,“还是咱中国好啊,把农业税都给我们免了,嘎嘎的好。我们哥几个以后少喝点儿酒,多活几年,得看看咱们国家以后是啥样的。”
偶尔喝高了的时候,徐福胜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纯正的俄罗斯族,你看我们这长相,黄头发、蓝眼睛。屯子里有的混血是茨冈族,黑头发、黑眼珠,相当于俄罗斯的吉普赛人,是受歧视的。”
消逝的民俗
除了黄头发、蓝眼睛,徐福胜一家没有一点儿像俄罗斯人的地方。
“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
凭借酷似欧洲人的相貌,徐福胜被找去当了几年特型演员,如今,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走过不少地方,“我在天津待了22天,宁波16天,舟山14天,东阳待了7天,后来就上横店去了……”走在马路上,徐福胜常被当成新疆人,卖羊肉串的新疆人硬是往他手里塞羊肉串。上街买水果,两块钱一斤的苹果,小贩当他是老外,愣是跟他要15块钱一斤。徐福胜一说话,小贩懵了,怎么满口东北话。
如今在整个宏疆村,几乎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村里的“音乐家”袁广荣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赛马》,抱起手风琴,却难以拉出一支完整的俄罗斯歌曲。
宏疆村村党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给一些俄罗斯混血的村民发了侨眷证,考学时能加点儿分。”
“入乡随俗嘛,当年跑去俄罗斯的中国人也都改成当地习惯了。”兵团村的王金财说。由于从小跟着母亲学俄语,1992年,王金财到俄罗斯当翻译,一待就是16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俄混血人,他爷爷是清末过去的。这个人就知道自己姓张,祖籍在山东,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还有一个姓苏的人,就因为有中国血统,1937年时被警察局抓去,人家让他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当时,这个姓苏的根本不敢露自己会说中国话。”
王金财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他在俄罗斯当翻译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个公文包。得知王金财是中国人后,对方说,过去两国的争论都怨赫鲁晓夫。王金财客气地表示感谢,“现在想想,他能这么说,不容易啊。”
王金财爱吃酸牛奶和酸面包,但妻子做不来酸面包,只得作罢。“要说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就剩这些了。”
天色由明到暗,老徐家的兄弟几个也从早喝到晚---早晨一大杯,中午两大杯,晚上两大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被打发着。屯子里一个叫张三的年轻人喝酒喝死了,说起张三,徐福河也会叼着烟叹息,但只要日子要过,酒就必须得喝。
边疆村的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屯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袁广军记得,那次寻亲之后,姑姑一家倒是又来过,他也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俄罗斯,但人走茶凉,现在也没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