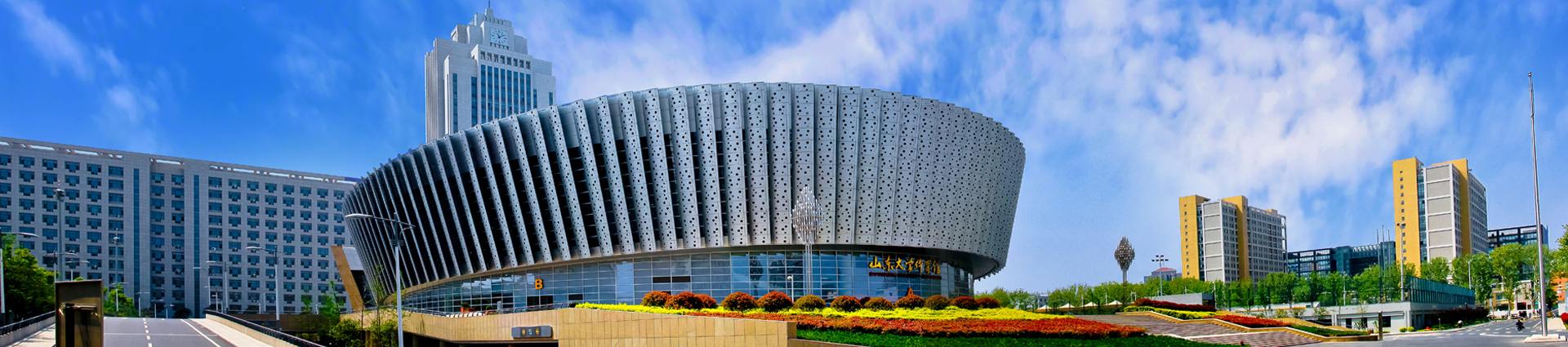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