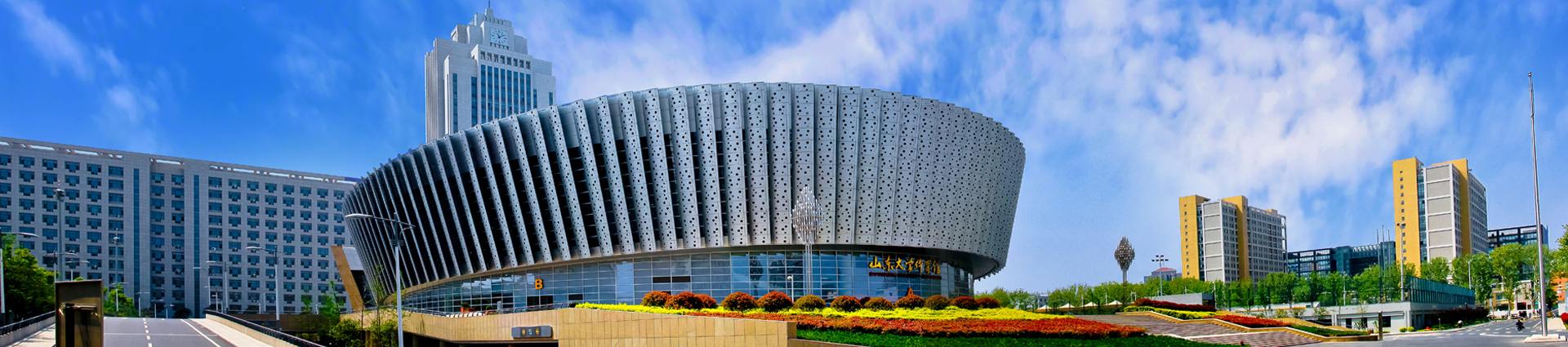随着叙利亚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中东难民和移民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冲击日益严重。默克尔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仅持续受到反对党的指责并且也受到了其党内的批评,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更是在考验德国政府的公信力。德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亦逐渐升温,“德国国家民主党”(NDP)和“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等极右翼势力借机开始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默克尔政府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不会改变其难民政策,只有计划将来自中东国家的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内进行再分配。默克尔的支持率自从去年以来已经严重下滑了二十个百分点,达到了欧元危机以来的一个新低。其实这并不是德国第一次在国内压力下接收外来难民。早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德国接收过人数达七十万左右的南斯拉夫难民,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都造成了一定规模的难民涌入德国。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则是德国包括整个欧洲由来已久的移民问题的一种较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它让很多人担心欧洲对于这一波新移民的“消化”问题。移民的融入问题不仅仅是移民政策的改变和经济机会意义上的问题,还有更为长远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 随着叙利亚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中东难民和移民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冲击日益严重。默克尔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仅持续受到反对党的指责并且也受到了其党内的批评,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更是在考验德国政府的公信力。德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亦逐渐升温,“德国国家民主党”(NDP)和“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等极右翼势力借机开始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默克尔政府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不会改变其难民政策,只有计划将来自中东国家的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内进行再分配。默克尔的支持率自从去年以来已经严重下滑了二十个百分点,达到了欧元危机以来的一个新低。其实这并不是德国第一次在国内压力下接收外来难民。早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德国接收过人数达七十万左右的南斯拉夫难民,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都造成了一定规模的难民涌入德国。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则是德国包括整个欧洲由来已久的移民问题的一种较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它让很多人担心欧洲对于这一波新移民的“消化”问题。移民的融入问题不仅仅是移民政策的改变和经济机会意义上的问题,还有更为长远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一书如今常常被拿来做来佐证不同文明的不可兼容性,今天中东国家移民和和欧洲社会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其实亨廷顿的原书并没有探讨这种国内多元文化的冲突,而关注的主要是国际间的所谓文明关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真正的文明的冲突是文明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来隐含的意思是指代表文明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和非民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当代更多的文明冲突往往都发生在国家内部,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种族冲突以及教派等冲突。今天的欧洲在成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情况下亦产生了多元文化冲突。近年来,从荷兰导演提奥·梵高因拍摄批评穆斯林社会女性状况题材的电影被害,到伦敦七七爆炸案再到丹麦卡通引发的抗议等标志性事件,都被解读为欧洲建设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失败。早在2010年,默克尔就声称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尝试在德国“绝对是失败了”,她在去年十二月的基民盟党大会上说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了“平行社会”,因此是个关于生活的“谎言”和“耻辱”。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的演讲中指出,国家支持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是鼓励了不同族群过着互相隔离的生活,并且这些互相隔离的族群正在挑战着英国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民族认同。
欧洲和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近几十年发展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现象,它往往包含着三层意义。它首先是指整个社会朝着具有更为多元化身份的方向发展的现象,即随着各种基于种族、性别和宗教等身份的不同族群逐渐增多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于移民接受国来说,具体主要表现在其国民人口结构及其相应的种族、语言和宗教特点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和新加坡都是多元文化社会。欧洲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浪潮,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构成。当年的西德因为经济发展需求从南欧、亚洲、中东国家如土耳其乃至东德大规模引进了移民补充其劳动力,而东欧国家如前南联盟和波兰等亦在冷战之后成为了重要的对德移民输出国。和其他欧洲移民接受国家类似的是,德国起初只是想利用这些移民的劳动力,并想让这些移民在工作结束后便回到自己的国家。德国人因此称这些移民为“客居工人”(Gastarbeiter)。然而,这些客居工人在德国长期居住了下来,他们的亲属也开始大规模移居德国。到了1980年代,这些劳工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后代也大量定居德国,标志着德国进入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德国改革后的国籍法案于2000年实施,加速了德国社会多元化的进程。据德国2014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其百分之二十的国民有移民背景,其中主要包括了来自东欧国家,中东国家以及中国等地的移民。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只是这两国接受的移民往往更多来自前殖民地如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等地。另一方面,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各异的移民逐渐开始形成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且在这些欧洲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平权运动。例如,土耳其裔是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他们通过参与德国政党和组织社团参与德国的政治,维护土耳其族群的利益。多元文化社会在为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福利、治安、文化习俗共处以及身份政治等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二个意义则指的是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往往和被称为社群主义的政治思想联系紧密。和传统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个体应该有相同的权利不同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群体的影响。它认为基于身份认同的族群有其独有的集体政治权利,它和女权、种族平权这样的思想息息相关。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少数族裔的权利在由强势的多数族裔主导的社会政治体系中容易被压制甚至剥夺,而这些少数社群的文化生存权需要被承认。例如,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只有单一语言的教育,那么就会让其他不说这种语言的少数族裔陷入相对弱势的教育境地,也违背了自由主义对于个体普适权利的平等假设。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用加拿大魁北克省作为例子,说明了魁北克省的法语法案帮助确保了法语族群的文化生存权。在他看来这种文化生存权和传统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生存和言论自由权是同样重要的。泰勒在其《承认的政治》一书中批评传统的自由主义在界定权利时运用了过于僵化的统一规则,并且常常怀疑和牺牲群体目标。泰勒认为在今天在更多的国家进入到多元文化状态后,传统自由主义的统一规则程序在实践中会越发变得不可行了。
印度裔英国学者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在其著作《反思文化多元主义》中则主张对西方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并认为不同的文化族群可以通过对话交流产生相同的普适权利。他同时也认为这样的对话交流需要言论自由、对于公共领域事务的相同参与权、基本的协商民主程序和道德规范等自由主义传统作为保障。多元文化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是它们一般都认为群体政治权利和个人政治权利同等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植根于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但今天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实并不在欧洲。其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和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恰恰都是加拿大人,而美国亦在多元文化主义领域拥有着一大批世界领先的优秀研究者。
多元文化主义还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指政府的社会公共政策。类似传统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区别,多元文化的社会公共政策区别于将移民族群和接收国主流族群一视同仁的同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强调通过国家权威确保不同族群的权益。例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多语种官方语言和学校教学、英国学校里为穆斯林设立的礼拜室和清真食堂,再或如允许锡克教徒在工作场所戴头巾而不用佩戴任何安全帽或者工作帽等都是属于多元文化范畴的政策。在实行较为同化政策的法国和德国,要获得长期居住权的移民必须通过两国官方语言以及主流社会价值的教育,另外像法国也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所穿戴罩袍等服饰。事实上,世界上将多元文化政策作为官方政策的国家并不多。最早出台该官方政策的是为了防止法语魁北克地区分离活动的加拿大政府,随后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也采用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学者威尔·金里卡曾和同事开发了一项“多元文化政策指数”来评估21个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出台情况。数据显示21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在近三十多年内变得更为倾向文化多元主义,虽然个别国家如荷兰以及意大利在这方面出现了倒退。同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此方面常年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各个欧洲国家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德国和法国均常年落后于英国、比利时和瑞典等国,这也说明德国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践上并没有走在其他国家前面。
在2000年之前,德国政府认为移民就是“没有问题的外国人”,尤其是数量庞大的非德国籍土耳其劳工。对于移民融入德国的问题,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话来说即是“在没有冲突和国籍的情况下变得契合德国的社会生活”。2000之后德国政府承认了需要真正的移民同化政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移民政策改革,出台了新的绿卡项目和所谓的“融入合同”项目。德国今天大致延续了这种同化政策,例如需要叙利亚等地的新移民接收德语和德国社会价值的教育后才能获得居留权等。
两种道路下的不确定未来
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一般指的是其政治思想和政策框架,这两点在近十几年来受到了持续的批评和挑战。曾于去年和泰勒一同获得克鲁格奖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对泰勒的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其主张的群体文化生存权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具有潜在的冲突。他举例说一个土耳其裔的移民女性如果出于宗教理由被其家庭认为不需要受某些公共教育,那么这种集体权利显然是对于个人自由权利是非法的侵害。哈贝马斯还认为,即使在这种集体文化权能够和个人权利相兼容的情况下,也没有足够理由认为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来保护这种集体文化权利。理由是该文化社群的后代可能会有想要退出该文化社群的情况,而想要退出的后代很可能因为国家法理的介入被剥夺了个人退出的权利。帕雷克也对于金里卡有着类似的批评。他认为金里卡的理论忽视了社群本身内部的多元化状态,社群内部的个人和社群之间应建立相对的权利关系来保证个人自由和社群集体权利的兼容性。
另一方面,对于多元文化政策的常见批评在于其制造了所谓的“平行社会”,也即由各个族群相互隔绝并存的聚居区社会形态。这些族群之间的互相隔离以及少数族群和主流社会之间的隔离不仅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明显社会经济差异,并且削弱了民族认同感。例如在英国伦敦,城市区域被切分成了非裔黑人聚集的东南部伦敦,以及印巴人聚集的西伦敦。这些族群首先认同的是他们的族群其次才是伦敦或者英国。英国的移民学生也更加倾向去只有自己社群成员和语言教学的学校,这样让移民后代融入主流社会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并不是多元文化政策下独有的状况。在实行更为同化性质政策的法国社会,移民群体往往生活在封闭和落后的郊区,酝酿了持续挑战法国的治安问题。在德国,近来的叙利亚新移民也更倾向居住的阿拉伯社群内。印度裔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者柯南·马里克(Kenan Malik)对此的看法是,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主义一样是为了应对碎片化社会的挑战,但是两者同样让社会更加碎片化和部落化。
近十几年来欧洲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更多集中于穆斯林社群,而穆斯林社群逐渐在不利的公共环境中变得越发封闭和保守化。关于某些穆斯林群体在公共场所戴头巾、女性教育以及一夫多妻等问题一直是公共争论的焦点。习俗问题上的讨论对于经历过其他多元文化冲击的欧洲来说并不特别新鲜,而在笔者看来欧洲面临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穆斯林社群内部的伊斯兰教法问题。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穆斯林社群主张将当地的穆斯林聚居区变为由宗教警察巡逻的伊斯兰教法区。而这样的宗教警察据说已经在西班牙出现,那里曾有一位女性被伊斯兰法庭以通奸的理由宣判为死刑,这位女性随后向警察寻求庇护。英国的穆斯林社群内部也存在着大量伊斯兰法庭,它们往往游离在官方法律边缘充当着仲裁社群成员家庭内部问题的角色。200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于伊斯兰教法可以补充民法的观点引起了英国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要求其辞职,直到他出面澄清自己并不是支持建立平行于英国现行法律的伊斯兰法体系才算平息。在德国,不仅穆斯林社群的伊斯兰法庭行驶的权力被包容为是少数族群的权利,并且非穆斯林的法官也会引用伊斯兰教法为一夫多妻制度以及对穆斯林女性的家暴等案件辩护。穆斯林社群的伊斯兰教法在实践中存在着和性别平等以及民主自由等西方主流价值上的深刻冲突,这种冲突是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的很大难题。同时,不同的穆斯林社群内部对于伊斯兰教法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这加大了国家权威介入界定伊斯兰教法权力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法对于穆斯林的影响可能被政治势力和极端主义利用,削弱了穆斯林社群对于移民接收国的民族认同感并加大了融入主流社会的难度。
对面对大规模中东难民涌入的情况下的欧洲国家来说,让穆斯林社群的内部制度及其实践更加遵循现代民主社会生活也显得越发现实和紧迫。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欧洲国家政府有能力更积极改善穆斯林社群和主流社会的关系,更何况出台更加严格的同化政策。也许今天的欧洲面对的不仅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而是多元文化主义和全面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确定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