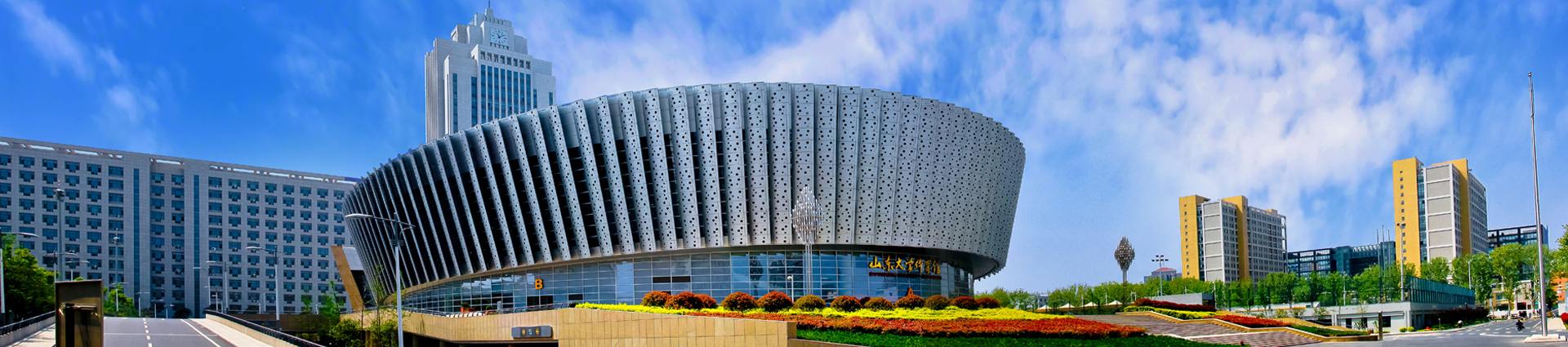正视跨境移民挑战,因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必然影响流入国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数以万计的世界贸易大国,我们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长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正视跨境移民挑战,因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必然影响流入国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数以万计的世界贸易大国,我们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长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高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应给予国际移民问题足够关注
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一方面,他们因与当地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高而更容易融入当地生活风俗、文化传统、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人数的明显劣势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体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虽多,但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陆续到来,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对当地有潜在敌意的单一移民群体,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陆续融入当地,或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挑战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膨胀到了很大数量,并以原国籍、民族、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移民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成员较多地倾向于通过指责当地规则和政治权威不公来获得更多利益和增进本群体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当地既定规则、服从当地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假如单一外来移民,特别是文化传统与当地主流社会差异较大的外来移民人数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只要东道国政治环境适宜,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对移入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治统一威胁最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进入的某个单一移民群体甚至可能在一个地区占据多数而“鸠占鹊巢”。
今天,不少国家在国际经贸发展和收容难民过程中,其国内陆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单一聚居外来移民群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针政策又激励了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拒绝融入当地社会,而围绕原国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具有或明或暗敌意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正日益成型并具备现实行动能力,而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会以暴乱等相当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假以时日,未必不会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对抗。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条件相同,内部统一性较高的社会在艰难困苦时更有凝聚力,而内部统一性较低的社会则往往只能共享乐难以共患难。二战之后,在西方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外来移民与东道国社会相对和谐,不等于现在和未来也和谐。因为彼时外来移民人数尚少,而且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饼”可以分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西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50.4%,仅中国一国就占15.4%,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1%);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低速增长期,且西方经济增长低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大饼”缩小,社会异质性却大大提高,必然驱使人们转向小集团身份认同,以求在资源竞争中取得助力,外来移民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同样,一些当前的高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不对国际移民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待到它们步入较长的经济减速期时,潜藏的矛盾纷纷凸显爆发,那时它们将可能面临束手无策的境地。
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利于外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的社会生活的困难和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且直接或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恰恰是这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降低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再次,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的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英国和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及其负面冲击已经在西欧国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思。西欧一些大国政要也公开抨击多元文化主义。但倘若没有经济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配合,他们的抨击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国内消费增长多年滞后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别国经验教训,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