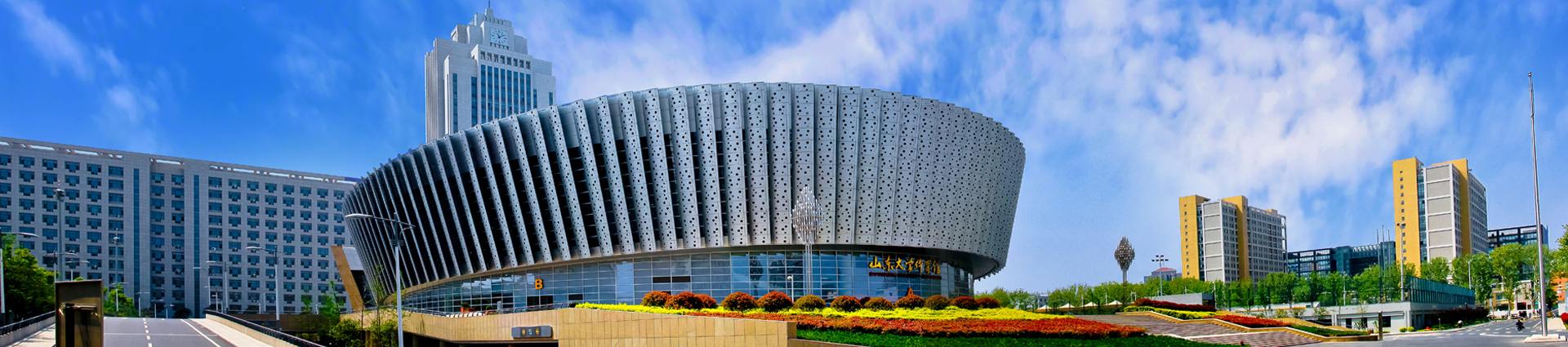农民工期望诉求的代际变化标志着农民工已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由“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 农民工期望诉求的代际变化标志着农民工已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由“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与性质发生了大的变化,有一个从“流动”向“移民”的变迁趋势。这一转化使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逐渐演变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即“流动者”的城市融入与“移民”的城市融入,二者所关联的市民化诉求是截然不同的。
“流动人口”与“移民”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公民权
“流动人口”与“移民”是两类异质性人群,区分二者的标准主要有“是否改变户籍关系”、“是否重新定居”、“人口与户籍是否分离”等。以户籍为核心的身份区分承载着差异性的城市公民权利,与流动人口相比,移民身份包含着可以获致的权利资格与正当性,享有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在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中,农民工大都被作为流动人口来对待,甚少被视为具有定居倾向的移民。由于政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放在“外来”和“流动”上,导致农村“流动人口”被广泛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以及各项公共服务之外,从而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近年来,中央与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改善农民工处境的政策规定,但由于其立足点仍是“流动人口”而非“移民”,因而并不涉及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权利的全面调整。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很难转化为移民。虽然各地都在积极倡导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具体到实践层面,却没有给予农民工彻底的城市化机会。各地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劳动力素质的竞争,出台更为严苛的、筛选性的城市移民政策,日益青睐高素质、技能型的流动人口。虽然许多进城农民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移民群体,但在制度框架内,从“流动”到移民仍然有着难以逾越的界线。
显然,在没有放开“移民”的情况下,“流动”只是一项不完整的权利。
“进入”与“定居”的分化
带来不同人群的城市融入问题
受特殊体制的影响,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与迁移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出现了“进入”与“定居”的阶段分离,由此衍生出两类人群的城市融入问题,即流动者的城市融入与移民的城市融入。前者发生于“进入—定居”阶段;后者发生于“定居—融入”阶段。“流动者”融城的关键是制度化进入问题,以实现城市稳定居住、获得户籍身份为目标;而“移民”融城的关键是文化心理适应问题,衡量的标准是身份认同的转化。
这既是不同人群的城市融入问题,也是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城市融入问题。当前,大多数农民工仍停留于“进入”阶段,还未完成“定居”目标,其城市融入至多只是一种浅层适应而非深层融入。事实上,只有在城市中实现了“定居”的农村人口,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城市融入问题。
首先,“融入”与“进入”具有不同的内涵。“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文化心理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进入”是指农民工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由“农”到“工”的转换,由于“进入”并不涉及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的深层适应,因而只是浅层的转换。无疑,“融入”比“进入”居于更高的层次。其次,“融入”与“进入”又不可分割。从农民工群体层面看,有一个“进入—适应—融入”的过程;从社会层面看,也有一个“抗拒—接纳—融合”的过程。进入城市是实现融入城市的开端,只有先“进入”,才有之后的“融入”。
显然,在未发生“进入”与“定居”的分化之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移民化趋势的进一步显现,“流动者(进入者)”的城市融入问题将逐渐上升为“移民(定居者)”的城市融入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远比流动者的城市融入问题更为复杂,将会对今后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更多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
有进一步加强移民的趋势
不流动的流动人口和长期性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种真实存在,他们更接近于事实上的移民群体。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壮大,农村流动人口日益表现出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移民倾向,并正在沿着从“流动”到“移民”的趋势发展。有研究者指出,“过去30年是农民工从流动开始向移民转变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对农民工的监测调查,有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农民工的移民倾向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另一组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流动的移民化倾向。多项调查表明,与代际更替紧密相关的是,农民工的流动方式已由个体式流动向家庭式流动转变。“北京城市流动人口移民倾向和行为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1984~2006年期间,北京外来农民工的家庭迁移发生比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举家外出的农民工逐年递增,且近年来有加快发展趋势。从2008~2011年,农民工举家外出人数增长了420万,增长率达14.7%;其中2010~2011年增长最为迅猛,在农民工总量增长4.4%的情况下,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达6.8%。虽然家庭迁移并不等同于定居迁移,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关于未来定居的打算,要大大高于未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这些都意味着,农民工流动的性质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从流动到移民的倾向将会进一步增强。
农民工在权利意识与诉求驱动下
正转向“移民政治”
城市管理政策的发展历来落后于农民工期望诉求的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实施严格的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老一代农民工围绕城乡间的“流动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不仅推动着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型,同时也促使城乡二元隔离的政策制度开始松动。从最开始的“盲流”到“民工潮”,再到“农民工”,如今农民工自由流动的权利已得到普遍的承认。然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诉求与权利意识的增长,仅仅是“流动权”的放开已无法满足其需求,向城市移民以及定居已成为一种日益凸显的趋势,其诉求也开始由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需要给予更多政策上的关注。农民工期望诉求的代际变化标志着农民工已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由“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曾一度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永久定居群体,对于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安排,老一代农民工大多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感、质疑甚至抗拒。不少研究证实,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较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进步,与此同时,诉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制度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有恶化的潜在风险。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更高,当维权受挫时会产生更强烈的参与集体行动的冲动。由于农民工一方面长期处于制度性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之外,另一方面组织化程度很低,缺乏合法的参与途径,在遇到问题时社会张力很小,成为最易爆发群体性事件的群体。
由于在“流动人口”的框架内已无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发展的市民化渴望,“移民”概念的引入为此提供了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它有助于拉平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推动农村流动人口的“制度化进入”,助其早日实现城市定居愿望,既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他们合法的城市公民身份,更要跟进社会服务建设,实现农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前既要处理好“流动者”的城市融入问题,更要准备好迎接“移民”的城市融入难题。理论上,这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两个层次;实践中,两者却是交错发生的,需要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