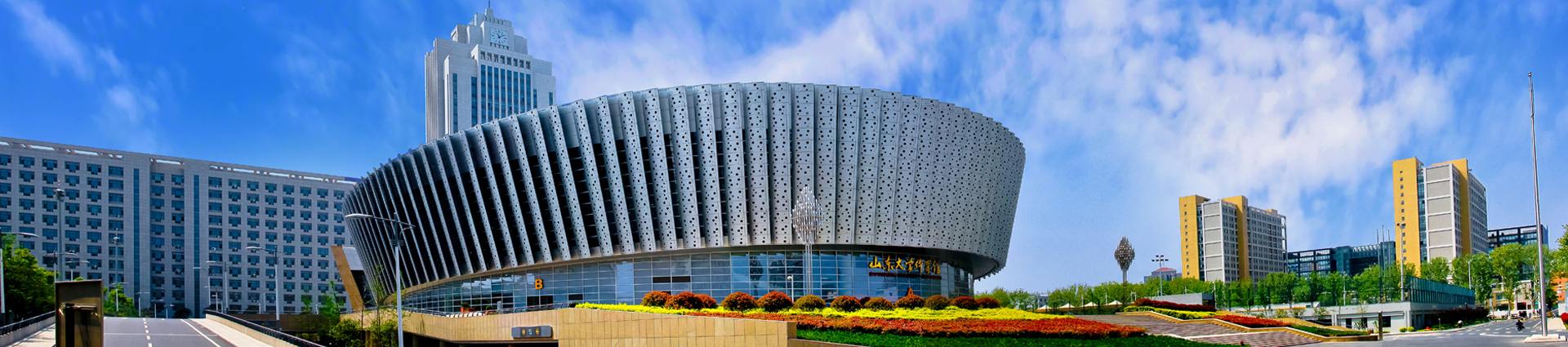【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文章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阐释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文章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阐释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关键词】中越边境 跨境民族 国家认同 跨境交易
边界:跨境民族的生存空间
国家、民族、边界一直是现代人类社会关注的热点。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权与国家关系的体现,所以边疆研究多是反映国家权力中心的意志。近年来,在全球化跨国流动的大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国家边界的观念被动摇,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迫切需要重新审视。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国家边界,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颇具权威性。韦伯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①,并明确指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以特定领土为疆域。换句话说,国家边界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此后关于边界的论述,基本上以韦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而国家边界的有无,也成了国家形态上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指标。正如吉登斯指出,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家边界②。传统国家由于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其行政范围没有延伸到在空间上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某些城市,也并没有延生到地方社会的实践中。传统国家的疆域是模糊的,并没有明确的界线。相反,吉登斯称现代民族国家为权力集装器,民族国家的行政控制能力加强,甚至能左右个人的日常活动。国家边界形成理论中,模糊不清的边陲转变为清晰准确的国家边界线已成为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体上都为文化族群的共同体,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重构并不是以传统的族群文化边界为国家领土边界,而是用界线将地球表面人为地、暴力地划分成不同区域,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跨境民族的产生。边界两侧的人们虽然无法共享现实的相同的国民身份,但他们共享历史和文化。由于彼此相互覆盖的生活半径被人为地划分在不同国家的领土上,探亲访友、跨境交易等社会经济互动行为成了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构成了边境民族最为重要的生活面相。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边界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政治分界线,而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文化内容在自然空间的叠加。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从政治角度看,国家边界是封闭的、不可逾越的,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国家边界又是开放的、相互渗透的。现如今的边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体现,而且是族群文化、国家认同感的反映。③边界已经超越国家领土的政治界线,在跨境族群文化、社会空间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意义。本文的中越边境既具有明确清楚的领土分界线,同时又具有跨境性的社会互动的多层次空间。而跨境民族则是了解复杂的边境社会、深入探讨国家与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关键。然而,目前研究中多将跨境民族作为在国家政治框架内建构的一种新的社会群体,着重于国家政治空间的建构对族群文化的重塑整合作用的研究,而跨境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国家边界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变化、跨境性的社会互动对国家政治空间产生的影响在学术探讨中并不多见。如边民跨境交易等社会经济互动行为,不管出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④,边境民族行动的自主性以及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笔者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并对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进行阐释,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解读中越边民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跨境互动行为,这不仅在现实中有助于民族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兴边惠民,构造有序的边境社会秩序,对边疆稳定、区域经济构建和民族融合有所裨益,而且在学术上对深入调查研究边境区域和跨境民族具有积极意义。
跨境交易:中越边民的社会常态表达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属于中华文明圈的国家。纵观越南约两千年的历史,前一千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下,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越南被称为交趾,是中国中央王朝统治下的郡县,因此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国与国的边界线概念。之后尽管越南摆脱中国的统治,建立自主封建王朝,但仍向中国纳贡,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此时的疆界划分并不清晰,仅仅是依照以前郡县的界线而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边界管理比较松散,而且双方彼此势力互有消长,疆界更多是处于一种有伸有缩、模糊不清的状态。
至19世纪末,中越边界的基本形态在与殖民者的交涉和斗争中逐渐形成。19世纪中期以来,越南遭受法国殖民主义侵略,1884年越南阮朝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投降条约,从而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5年中法战争后,当时的清政府与法国交涉越南事宜,并就中越边界线签署了包括《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在内的一系列条约。1886年到1897年,中法两国按照条约勘定中越陆地边界,并在边界上树立了300多块界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边界走向,⑤从此中越边界以条约的形成取得了法律认同,纳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范畴。从模糊边界演变为现代意义的清晰条约边界的同时,边界被赋予了国家属性,具有了捍卫主权国家、不容侵犯的特性。中越两国绵延1353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两侧居住着12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生居区域直接跨越中越边界,民族同源,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习俗,跨境性的社会互动是中越边民的传统交往方式,是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由于国家权力较少渗透以及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中越边境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这一时期国家边界对中越边民来说并无太大意义。
之后,越南虽然于1945年发动“八月起义”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频繁遭遇战事,法国的卷土重来,越南南北的分裂,直至1976年才重新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越两国政府关系密切,外交关系整体上比较友好,双方从未真正触及勘界问题,边防管理也不甚严密。中越边民的传统交往方式虽然开始有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但总体上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彼此跨境交往几乎畅通无阻。历史上的中越跨境交易,绝大多数出于民间贸易,两国边民之间货物商品互通有无,对改善边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边境稳定,睦邻友好。
中越战争时期的边民跨境交易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美苏两国势力的介入下中越关系空前紧张,边境地区军事化管理加强。中越边民的社会生活中,政治因素的制约远远超过血缘、地缘等因素。国家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社会交往被限定于国界线之内。比如,战争前后,中越边境上埋藏了数百万枚地雷,密度高加之边境地形复杂,中越边境地区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中越边境成了不可逾越的国界线。国家政治力量的渗透,强化着当地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同时跨境往来也受到约束,生活范围逐渐被限制自己国家的边界之内。
但事实上,紧张敌对的两国关系虽然使得边境贸易一时处于停滞状态,跨境流动并非完全中断。从笔者调查中得知,即便在中越战争期间,边界两侧民众的跨境往来也并没有停止。走山野小路探亲访友,还互相告知哪里埋有地雷。跨境往来不单单是亲戚走访,还进行着跨境交易。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如中国,越南边民生活也比中国边民贫困。由于生活圈跨越中国和越南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共同的生活、经济需求成为边民跨境往来的促动力,越南边民自发地涌入中国边境,同中国边民进行商品交换、互通有无,在边境线上形成了多处草皮街。
滇越边境上,1979年下半年,边民之间的物物交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中国人用缝纫、棉布、热水瓶、手电筒、塑料鞋、清凉油等,和越南人的蔬菜瓜果、草药药材、家禽蛋类进行交换。⑥据《河口县志》记载,边境山地的桥头乡有草皮街,双方边民在此进行交易。而在桂越边境上,从1982年开始,越南人拿着鸡鸭等来到中国境内,交换中国人的布、手电筒、药品、解放鞋、酒等。根据边境场所的不同,恢复交易的时期也有所出入,但双方边民突破边境的军事封锁线跨境进行交易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此,越南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跨境往来。1984年3月,越南内务省发布了严格控制边界的相关条文,前往边境地区的人员需取得特别通行证,前往边界前线则需要居住当地乡书记、主席的允许和签字,擅自跨境者被处以罚款劳改等。即便如此,跨境民间交易的规模仍在逐渐扩大,国家行为已经不能限制,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国家默认了这种行为。1988年11月19日,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公布一百一十八号通知,正式承认边境居民跨境访亲、交换生活所需用品。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至此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紧张对立关系,双方就设立正式的国家级、省级口岸与多个边民互市点达成协议。
通常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使得国家边界变得容易渗透,中越边境贸易的恢复对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其背后,中越边民的自主的行为,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边民来说,虽然各自持有中国和越南两个不同的国家身份,但生活区域跨越两个不同的国家,战争并没有完全割离跨境民族之间一直持续的社会经济交往。即使在中越两国关系紧张的战争时期,边民的跨境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也并非完全中断,两国边民之间的互助交往仍然持续着。边民自主进行跨境交易并不是意图颠覆国家主权,而是在国家政治框架下一种自我调整的生存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边民跨境交易
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边民的跨境往来更为活跃。随着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在边境地区的逐步展开,以及越南1986年革新开放政策在北部山区的展开,中越边民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打通了由国家政治权力构筑起来的界限。通常,边境的重新开放容易被误认为完全自由化,其实不然。跨境民族的生存空间面临的是一次新的更为复杂的整合。
中越两国先后陆续开放了对开的口岸和互市点,截至2010年5月,中越边境设有口岸9个,而边民互市点达到54个,其中广西25个、云南29个。同时,两国签订一系列经贸协定,边境贸易的开展形式、商品种类、交易规模等管理体制也日益规范。针对不同种类的贸易类型实施不同的出入境或税收政策。边境贸易制度的规范化,也意味着在边境管理中国家政治力量的渗透,如此前引用的吉登斯的论述,国家作为权力集装器,甚至能左右个人的日常活动。
与中越边民的直接利益相关的是两国政府对边民互市制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出入境方面,双方边民只须出示边民通行证即可;在关税方面,中国规定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在3000元以下的免征关税,同样越南规定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在200万越盾以下的免征关税。相比较一般边境贸易,边民的跨境交易即边民互市更加灵活、变通。
在云南河口随处可见越南边民的身影。越南老街的一些妇女将采摘的山菜草药拿到河口的农贸菜市场出售,或从河口批发日用品到越南做小生意。而越南老街的猛康,地处山区,相比较越南国内,与接壤的中国边境地区联系更为密切。猛康的定期集日上还可见云南河口边民的身影,他们大多出售水稻种子、化肥农药、农活器具等。这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越南本国供给少质量差,所以中国边民的赶集摊位颇受越南边民的喜欢。
值得注意的是,边民的另一种参与边境贸易的方式—“搬运工”。在云南河口,大批的越南边民肩挑担扛地将中国物品运到越南,他们并不是商人,而是受雇于商人的搬运工。因为物品经边民之手可视为通过边民互市进口的,享受边民互市的关税优惠。边民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雇佣机会。越南边民们也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边民的优势,乐意受雇为搬运工,赚取现金收入。
不管是原有的边民互市的参与者,还是搬运工,他们从国家的边境政策中获得切身的物质实惠,进而逐渐培养了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结语
中越边境社会有不可逾越的边界线,又是跨境性的社会互动的多层次空间。跨境性的社会互动是中越边民的传统交往方式,是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本文实证地呈现中越边民真实的跨境交易的社会互动面相。民族国家在建构自我边界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许多影响。一方面,边界划定、边界上国家机构的设立、甚至战争冲突等使得跨境民族的国家观念逐渐上升。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框架下,中越边民自主地进行调整生存策略,即使在中越两国关系紧张的战争时期,两国边民之间的传统的互助交往仍然持续着,同时这种跨境性的社会互动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边境贸易制度的规范化,也意味着在边境管理中国家政治力量的渗透在不断加强。而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边民互市,中越边民从国家行为中得到了相应的经济利益,产生归属国的意识,提高了国家认同感。
【作者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政策媒体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③Hastings Donnan and Thomas M. Wilson. Borders: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1999, p4.
④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年第5期。
⑤李桂华,齐鹏飞:“中越边界问题研究述略”,《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92页。
⑥黄永祥:“金平草皮街走向大市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17页。
责编/张晓
|